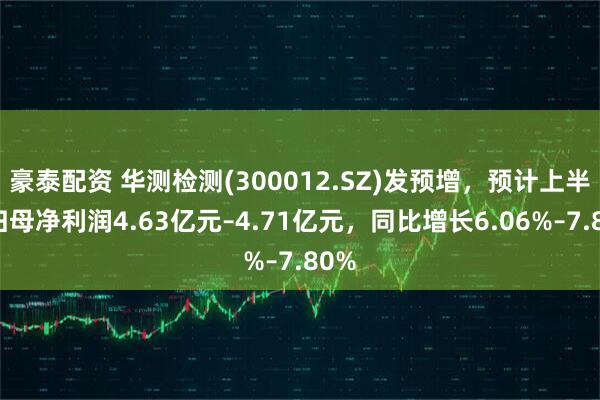在聆听朱煜老师课文文本解读第二讲的过程中,我深受启发,对好文章、好词好句的认知发生了极大转变。课文文本解读直指教学的核心——观念的革新。教师先成为 “语言的明白人”富豪配资,才能引导学生成为“语言的感受者与运用者”。
从“记定义” 到 “悟语境”,让词语 “活” 起来
上学时,“摘抄好词好句” 是语文学习的固定作业,可 “好词” 的标准却始终模糊。朱老师的解读让我明白词语的价值不在华丽,而在贴切。
《桂花雨》中“桂花树的样子笨笨的,不像梅树那样有姿态”,“笨笨的” 一词从字面上看,并不优美,极为平常,却写出了作者对桂花树的喜爱。
教学中朱老师设计 “词语替换对比” 活动,让学生将 “笨笨的” 换成 “笨的”,学生很容易发现,只有 “笨笨的” 能带出 “憨厚、亲切” 的独特韵味,与梅树的 “姿态” 形成巧妙反差,凸显作者的偏爱。
对词语的理解,历来有争论。即使到今天,仍然有不少老师习惯于让学生熟记词语的解释、定义。但这样的背诵意义不大,比如,“缓和” 在词典中解释为 “和缓”、“服从” 解释为 “遵照”,这样的循环解释对学生而言毫无意义;“启发” 的学术定义再熟练,小学生也不能真正领会。
展开剩余69%朱老师在解读《蟋蟀的住宅》时,为我们示范了更具说服力的教学路径,当讲到 “蟋蟀和它们不同,不肯随遇而安”,先引导学生观察蟋蟀如何慎重选择住址,再理解 “它不肯利用现成的洞穴” 的行为。此时 “随遇而安” 的含义就自然浮现,远比背诵词典定义更深刻。
从“看修辞” 到 “品逻辑”富豪配资,让句子 “立” 起来
以往,我习惯于以是否使用四字词语、是否运用比喻、拟人等修辞手法来判定句子的好坏。但朱老师的解读让我明白,好句的核心在于能否精准传达作者彼时彼刻的情感与意图,修辞手法只是情感表达的工具,而非目的。
比如《荷花》课文中,作者为表达对荷花的喜爱,将自己想象成一株荷花。
比如《盘古开天地》一文中“天每天升高一丈,地每天加厚一丈”“清而轻的东西,缓缓上升,变成了天;重而浊的东西,慢慢下降,变成了地” 这些看似朴素的句子,实则延续了传统中文的韵律美,吸收了文言文的凝练特质,教学中让学生反复朗读,感受句式的对称与节奏,远比分析 “有没有修辞” 更有价值。
再如《女娲补天》一文中第三自然段段首为 “这可是一项巨大而又艰难的工作”,朱老师引导大家在课文中寻找 “巨大” 与 “艰难” 的具体体现。“巨大” 体现在步骤繁多,“艰难” 体现在每一步的实施不易。这种将句子与上下文逻辑关联的分析,让学生既理解了句意,又把握了课文内容。
理解了句子的优美,老师可以根据学情设计相应的练习,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句子的魅力,提升对句子的理解和运用能力。
从“拆段落” 到 “追脉络”,让篇章 “连” 起来
不仅词语、句子的教学如此,篇章教学更是这样。叶圣陶先生说篇章要调顺“内面的意思情感是浑凝的,有如球,在同一瞬间可以感知整个的含蕴;而语言文字是连续的,有如线,须一贯而下,方能表达全体的内容。”
按照这个标准,我们来看《繁星》这篇课文,会发现文章的最后一句:“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子,现在虽在母亲的怀里了。” 有些突兀,为什么会突然讲 “母亲的怀抱” 呢?
篇章是情感与逻辑的统一体,每一句话、每一段落都是为整体表达服务的。我们不能将篇章拆解为孤立的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,更不能迷信教材,而应该引导学生 “瞻前顾后”,梳理篇章的情感脉络和逻辑关联,还原作者的表达意图。
朱老师的解读,本质上是让语文学习回归“人” 的层面,语言是“人表达自己” 的工具。
任何教学改革,在源头和根子上,都是观念的变革,而非策略、方法与技术的变革。
因此我们在语文教学中,要先改变观念,成为“语言的明白人”,建立正确的理念,然后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、学生或教学的时空,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,这样才能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。
扫码可见课程富豪配资
发布于:上海市垒富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